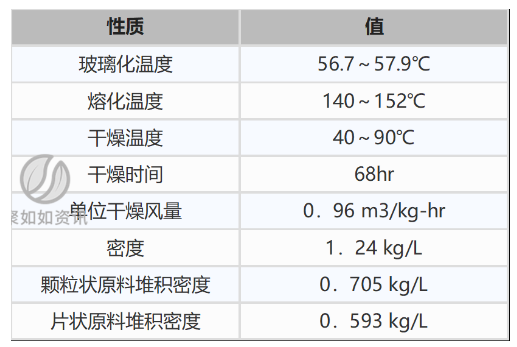重要新聞:“尼日利亞探索發現產塑料大米”
近日“尼日利亞探索發現產塑料大米”的新聞報道被如火如荼地蹭熱點了一番――準確說,是蹭熱點了3輪。
第一輪相對來說較不“受歡迎”,空穴來風是一個沒名氣的韓國新聞網址,稱“尼日利亞探索發現產塑料大米”、“外包裝袋子標出稻米,開啟確是塑料顆粒”、“做飯樣子顯著不對”,等等,這種新聞報道被全球一些漢語新聞媒體、網址和網上平臺轉截,但大部分波瀾不興。
第二輪則是“新聞報道關注度”承前啟后的重要:某知名華籍女新聞人從國外“異類”中文傳媒《大XX時報》上見到這則逸聞,在未作充足調研的狀況下運用自身的服務平臺和知名度開展“夾敘夾議”,乃至將之延伸到“食品衛生安全”等難題上,引起全球眾多中國人的高寬比關心和熱情探討。
第三輪則是第二輪的邊際效益:BBC分享了該華籍女新聞人的“夾敘夾議”,不但令這一“受歡迎新聞報道”一下具備了“國際性知名度”,還“出口轉內銷”在我國中國刮起更高驚濤駭浪――終究,這位華籍女新聞媒體人到報導素養等層面一直存有異議,但BBC確是較具公信度的知名國際性文化傳媒。
殊不知從第一輪起就持續有東西方人員提出異議:生意人是趨利的,用塑料生產制造“假大米”這類“低值易耗”,可以說用高端天然水晶石假冒一般光伏玻璃,總數又這般極大,簡直要賠得哇哇大哭?
一些在西非定居、工作中,或從業過這些方面業務流程的人逐漸在各網上平臺講解、回應,但知名度與“塑料大米說”、“食品衛生安全說”對比,可以說人微言輕、基本上聽不到氣息。
那麼,這到底是如何一回事兒?
非州最腐壞國家的“袋子標準”
小編自1992年起就從業對西非的外貿行業,且從“兄弟”到“老總”,從貯運、報關單證到一線(西非)銷售員都做了,小編的老婆則是從業國際性船務代理20年的“老資格”,針對這一“塑料大米”,是一點也不生疏的。實際上這也并不是什么“新鮮事物”。
尼日利亞是非州人口最多的國家,也是西非現代化水平最大、整體消費力最強的國家。但于此同時,它也是“老非州”、“老出口外貿”認可的非州最腐壞國家。這一國家的腐壞反映在人、貨“進出口貿易”行業,便是“袋子標準”的泛濫成災。
什么叫“袋子標準”?
簡易說,便是在櫥柜臺面標準上要求了成千上萬的“不允許”,很多很普遍的進出口貿易貨品,都“肯定”不允許進口或出入口,但事實上這種貨品一直在源源不絕地進口、出入口,并在本地銷售市場占有肯定壟斷性影響力。往往這般,是為了更好地給大操大辦單位和大操大辦者空出濫用權力的延展性,提升附加收益。
就以小編曾長期性從業的紡織產品來講,尼日利亞最熱銷的各種各樣亞、歐進口紡織產品種類,如蠟染平紋布、絞綜布、尺寸全方位提花面料等,在“櫥柜臺面”上全是禁止進口的,但事實上某國銷售市場上每一個月動則幾百、百余貨箱的這種紡織產品,絕大部分是進口的,只必須找一位神通廣大的“出口報關人”,走一套繁雜且成本頗豐的“要求程序流程”,這種貨就可以落落大方運進去。說白了“限令”,實際上但是給經辦人員“口”提升個收費標準敲章的原因而已。
但這還并不是難題的所有:由于早已進口的貨品在理論上依然是“走私貨”的,海關放行企業倘和發貨人或其他哪些關系人一時難受,隨時隨地很有可能托詞“緝私”再來一個不講情面;尼日利亞政出多門,就貨品進口階段來講,中國海關、警員、為名上歸屬于中國海關其實自行其是的“緝私中隊”、中國商務部、州和市二級政府部門……都有權利有工作能力在自身“眼底下”瞎折騰這些“水貨”,小編在尼日利亞周邊國家――貝寧經濟發展北京首都科托努時,幾個熟悉的同行業都會尼經濟發展北京首都拉各斯遇上最不幸的事(約2003或2004年間的事):由于國家商務部和緝私中隊間鬧別扭,后面一種將前面一種海關放行、不久進倉的幾十個紡織產品貨箱被查封,瞎折騰了個把月,發貨人花些價格贖出,前面緝私中隊封口揭下,后面一種國家商務部封口又貼上――之前繳錢算不上,還得再說一回。
即然市場監管這般錯亂,緣何也有那么多生意人相見恨晚?
“臺表面”的稻米,“櫥柜臺面下”的塑料
尼日利亞是西非最具魅力、銷售市場消費力令人震驚的國家,且很多商品毛利率非常大,因而就算成本昂貴、風險性頗豐,大部分“老非州”仍不舍得吐出來這方面不容易咽下的“贅肉”。實際上小編在貝寧科托努、多哥洛美的門市部,很多業務流程也依然來源于尼日利亞――該國小代銷商自身入境小批量生產選購再自主帶回,對大銷售商來講風險性就被轉嫁給和平攤了。但這類營銷模式,產品報價上沒有核心競爭力,且并不是哪些產品都合適。
文章開頭提及的塑料就歸屬于“不宜”的一類:它是化工原料,并不是日用品,難以“零打碎敲”,只有咬著牙“立即闖”――“塑料大米”就應時而生。
簡易說,“塑料大米”從一開始便是在出入口塑料,而不是稻米,往往要報“稻米”,則是由于稻米歸屬于尼“臺表面”能夠 合理合法進口的商品,而塑料則只有像前邊提及的紡織產品那般走“櫥柜臺面下”。以塑料假冒稻米看起來“高危”,其實要是“監督”這一個階段出不來難題就基本上再無后遺癥,在默認設置“走一步就需要花一步錢”的尼日利亞不但“多快好省”,并且簡約少風險性(只和一個階段相處);反過來,踏踏實實報塑料,則不但“監督”階段一分不省(進口“假大米”是“走私貨”,進口“真塑料”一樣是走私貨),并且也要附加和大量“現管”相處、通骨節,不但花銷多,并且風險管控更為艱難,“兩害相權取其輕”,做為西非塑料原材料消耗量較大 的國家,進口貿易公司如何選擇,顯而易見。
我本人第一次接觸“塑料大米”業務流程,是1992年的事,那時候在浙江省某國營企業荼葉貿易公司任單證員,具體做該筆做生意的,則是掛證我企業的一個余姚個人小公司(當初外貿體制未放寬,小公司無直營進出口經營權)。之后我一位寧波市籍高校同學靠做這一還發過大財。
當初的“塑料顆粒”,主要是價錢和級別較低的聚丙稀顆粒,但一些仍在西非的同行業詳細介紹,伴隨著尼日利亞現代化水平的提升,級別較高、價錢偏貴的各種高壓聚乙烯顆粒,乃至稱為“塑料王”的聚四氟乙烯顆粒也“添加戰團”。
因為風險性較高,當初中國大企業非常少染指這類業務流程,主要是“事在人為”的小零售商和小生產廠家在搞。近些年態勢有非常大不一樣,進口商經常是在非州當地或阿聯酋迪拜、加那利群島申請注冊的,從我國訂購時標出是“塑料顆粒”,但收件人卻在尼日利亞海外,待貨品從我國出口后,到達站變更、合同書和提貨單轉簽,“塑料”搖身一變變作“稻米”再運到真實的到達站――尼日利亞的拉各斯或哈庫特港。
那樣的“瞞天過海”,我國中國的生產商和出口公司是不是知情人或相互配合?如前所述,最開始這些“掛證”者不但知情人,并且便是具體主犯。但現如今的狀況照一位盆友的說規律“很繁雜”,不僅有知情人、參加者,也是有徹底被不在乎的說說、既不知道自身的貨品最后到達站是尼日利亞,更不知道好好塑料顆粒會被捆綁進稻米袋子的。
那樣的“塑料大米”做生意不斷了多少年?不清楚,就是以自己親身經歷來講就會有20很多年歷史時間了,且事實上輸出國也遠遠不止我國一家。雖然這期內“內函”、“外延性”都是有非常大轉變,但“做生意”自身一直存有,且“塑料大米”幾乎就被發貨人作為塑料來引入、市場銷售或應用,而不太可能去用于假冒稻米――就算最劃算的pe顆粒,價錢也多倍于稻米。

說白了“塑料大米”被查
自媒體時代讓真知“越辯越暗”
即然是心領神會的“半黑半白交易”,緣何忽然被查?如前所述,尼日利亞腐壞猖狂且政出多門(中國某大國際航空公司曾設立廣州市-拉各斯直航航道,試飛時尼總領事親自辦理托運隨員,緣故是“擔憂拉各斯中國海關高官不認北京市大使館審簽的簽證辦理、給試飛典禮丟人”,互相制約情狀可見一斑),一旦某一層面“擺高低不平”,就很有可能有些人“橫插一杠”,擺脫“內幕”再來一個“不講情面”。一般而言,這類“不講情面”會伴隨著“人情世故及時”,再次修復到“內幕”趨勢,終究尼日利亞百業待興,事實上是必須進口各式各樣的“嚴禁進口”商品的。但這一次“塑料大米”被不明就里的國外新聞記者抓個正著,又被一系列更“非專業”且自以為是的“二傳手”、“三傳手”3D渲染演譯,最后弄出那么個“驚世新聞報道”來。
連日來一些同意“回應”的新聞媒體、單位支支吾吾,緣故繁雜,不僅有“不了解”、“不技術專業”的難題,也是有一些事實上了解且技術專業的單位、人員麻煩難以啟齒的關聯(盡管尼日利亞的“黑海關清關”難題和烏克蘭相近難題一樣,是和本地銷售市場具體情況密切相關的“內幕”,圈里一般是可以原諒的,但終究“上不可櫥柜臺面”),而“自媒體時代”媒體專業素養、特別是在技術專業心態的比較嚴重“返祖”,則讓真知再度“越辯越暗”。
很顯而易見,此次惡性事件和“食品衛生安全”不相干,由于無論顧客、商家,都沒準備將“塑料大米”那么貴的貨品當谷物吞掉或賣出。
中國是尼日利亞最重要的貿易國,假如說,昔日對“黑海關清關”、對尼日利亞獨特的“袋子標準”,基本上全部尼日利亞的洲外貿易國挑選默認設置事出有因,那麼時迄今日,也許不僅有必需、也是有工作能力借助國際性行駛的貿易標準,和這一非州第一人口大國“好好地談一談”,唯這般,才可以讓將來輸往某國的塑料依然做塑料,稻米依然做稻米。